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论坛
文章编号:1001-2397(2019)05-0182-13
变数与前景:中美对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选择之分殊
徐崇利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开始从以往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转向现在对“权力霸权模式”的偏好,将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制度化程度的选择,从“规则倾向性”降至“契约倾向性”,从而为谋取自身现时利益最大化释放了美国权力优势运用的空间,构成对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反动,并投下了最大的变数。然则,脱离霸权统治,回归治理本位,以“制度导向”为模式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得以存续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立基于国家间合作伙伴关系及互利共赢原则而创建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方案,以“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经济治理新体制的探索最为典型。
关键词:国际经济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经济法;美国霸权;“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5.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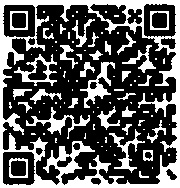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对于国际治理体系,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开始从以往偏好“制度霸权模式”转向现在偏好“权力霸权模式”,这样的偏好变化最典型地体现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二战之后,国际经济治理一直具有制度密集的特点。然则时至当下,国际经济领域已成为特朗普政府运用强权谋取美国现时利益的一大要地。如何看待美国此等变数的产生、性质及其对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有了美国此等变数,为维护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各国应如何应对?尤其是中国应当如何努力?这些都是当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国际经济治理模式与美国的偏好、选择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霸权国偏好的国际秩序可能有两种原生样态——“霸权秩序”和“宪政秩序”
[1]21。前者是指霸权国依仗自己的强权,以等级制的方式统治他国从而形成的一种国际秩序。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本文称之为“权力霸权模式”。后者是指霸权国接受制度性约束,相对成就国际关系“法治”状态的一种国际秩序。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本文称之为“制度霸权模式”。
(一)美国偏好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
对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霸权国到底是偏好“权力霸权模式”,还是偏好“制度霸权模式”,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霸权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形成的权力优势程度。申言之,当霸权国经济实力处于上升期,较之其他国家具有巨大权力优势之时,就会考虑长远利益,偏好“制度霸权模式”;反之,当霸权国经济实力处于衰退期,较之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趋于缩减之时,则会关注现实利益,偏好“权力霸权模式”。
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迁一般出现在大战胜利之后或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之后等关键性历史节点。在二战结束和冷战终结两大关键性历史节点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国的权力优势无时不处于巅峰状态,故当时就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偏好均为“制度霸权模式”。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制度基础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冷战终结,在美国主导下,再次扩大和强化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基础。在国际贸易领域,从传统GATT到WTO的发展,最为典型。
彼时,美国作为强势的霸权国,偏好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霸权模式”,乃是基于其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
[2][3]:第一,国际制度具有降低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长期功效。相对于更多地由美国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霸权模式”,在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当美国将制度充当一种治理的手段时,制度可以起到降低管理成本的效用;当制度作为克服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合作障碍的工具时,制度又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第二,国际制度可以保证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权力霸权模式”下,霸权国凭借自己的强权对其他国家直接进行统治,或可获得一时暴利,但采用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制度的持久锁定,美国可对权力进行长期投资,不断收取细水长流式的回报。第三,国际制度可强化护持权力地位的正当性。国际经济治理以制度为基础,可使小国也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并可产生比较平等的收益分配结果,从而降低小国对美国发起挑战的可能性,从而将小国的这种挑战压力转移到制度上,而不是像在“权力霸权模式”下那样直接针对美国。
然而,在美国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下,即使美国是世界经济霸主,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概凭美国的单方意愿。“与一种帝国的权力不同,霸权国在没有获得其他主权国家一定程度同意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制定和实施规则的。”
[4]46为了保证自身长远利益的实现,美国要让其他国家接受国际制度,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一是为维持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以便从长远意义上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取得更加稳定、持久的收益,美国须让渡一些眼前利益给其他国家;二是采取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将不得不保持相当程度的“权力克制”,以便让其他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过程。此外,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来看,美国作为霸权国,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最大“利益攸关者”,对于国际经济治理中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负有主要责任。
显然,只有自身经济实力处于上升期,相对其他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之时,美国才有足够的“实力剩余”,承担提供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相应成本,对其他国家让渡一些眼前利益和决策权力,并在作出这样的成本承担和收益让渡之后仍无伤自身的权力优势
[1]65-67。当然,为了实现前述高度制度化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下的长远利益,美国付出这样的成本承担和收益让渡之代价,终将是值得的。因此,当美国具有超群的经济实力之时,从长计议的结果,就会偏好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霸权模式”。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堪比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大变革的又一关键性节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美国的霸权地位客观上出现了衰退之势。然而,对于美国霸权地位衰退的程度,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主观认知大有区别,从而构建了美国前后两任政府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之不同模式偏好。
奥巴马政府认为,虽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相对下降,但对其他国家仍然保有相当大的权力优势。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奥巴马政府继续维持美国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主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等,极力打造美国等发达国家青睐的新一代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即属典型一例。
然而,较之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实力优势已趋衰减的认知可能要强烈得多。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其潜台词多少反映了其对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焦虑。一旦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有了如此强烈的认知,美国在战略选择上便会出现“近视效应”——更多地顾及美国的现时利益,并更加注重维持美国既有的权力地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之要义即在于此。既然认定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着不保的现实危险,特朗普政府就会“舍远求近”,不再优先关注高度制度化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下美国的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美国现时利益的最大化。质言之,因自身实力下降,美国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难以支撑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例如,要维持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制,美国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他国开放本国的国内市场。一旦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继续如此为之已使自己不堪重负,就会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放弃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逃避本应承担的生产和维持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
从另一角度观之,为了实现美国现时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权力优势,由此需要将国际制度对美国权力的约束降到最低限度。缘此,特朗普政府就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已开始偏好“权力霸权模式”,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抛开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大肆对中国等其他国家单边推行加征关税等贸易霸凌主义。
(二)美国选择的国际经济治理样态
当然,在国际经济领域,“权力霸权”与“制度霸权”只是两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现实中,霸权国实际选择的任何一种国际经济治理样态,都不可能绝对依仗权力而完全排斥制度,也不可能绝对依靠制度而完全排除权力。鉴此,本文所称的“制度霸权模式”,仅是霸权国处于强盛期的一种偏好,其实际选择的只能是这种模式之变种,即虽然霸权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但仍然以其权力优势作为后盾;同样,本文所称的“权力霸权模式”,也仅是霸权国处于衰退期的另一种偏好,其实际选择的也只是这种模式之变种,即虽然霸权国强调权力优势为其优先使用的统治手段,但不可能完全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易言之,从奥巴马政府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到特朗普政府对“权力霸权模式”的偏好,从权力层面来看,实为美国对权力优势运用的增强;从制度层面来看,表现为美国受到的制度性约束大为缩减。具体而言,以制度主体的开放性、标准的一致性和内容的稳定性等变量为判断基准,美国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之制度化程度的选择,已经发生了从“规则倾向性”样态降至“契约倾向性”样态的显著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客观上呈相对衰弱之势。因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之制度化程度的选择已开始有所降低,尤其表现在主体开放性之变量上,制度的“规则倾向性”已趋于弱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丧失了在多边层面大力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政治意愿和动力,把不再充裕的权力资源用在刀刃上,选择自己仍然占据实力优势的区域范围或诸边形式,构建局域性的国际经济治理新体制,诸如TPP、TTIP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简称TISA)等。
然则,奥巴马政府毕竟在主观上依然认定美国的权力霸权优势犹在,故其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下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总体上看,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规则倾向性”:一方面,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并未挑战以WTO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规则倾向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当时推动建立的局域性国际经济治理新体制,按照标准的一致性和内容的稳定性之变量判断,其“规则倾向性”仍属明显。诸如,就TPP、TTIP及TISA而言,美国的目标是其在国际经济自由化“高标准、宽覆盖”等核心特征上标准的高度一致和内容的正常稳定。即使在主体的开放性之变量上,美国也并非要将TPP、TTIP及TISA确立的规则永久地囿于区域范围或诸边形式,而是意在通过推行“从小到大”的战略,谋求有朝一日将之广泛扩张至全球层面,遂成一种多边体制,以使美国最终重回主导21世纪国际经济治理新规则制定的高地
[1]。
如果说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主要是在主体的开放性这一变量上降低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规则倾向性”,那么,特朗普政府因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有了更为强烈的认知,则是在主体的开放性、标准的一致性和内容的稳定性三大变量上,悉数降低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其偏好的是“权力霸权模式”。正因有此偏好,特朗普政府实际选择的是“契约倾向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借此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特朗普政府便可将美国对自身强权的运用,从规则这一更高强度的制度化约束中解放出来,以便有效地实现美国的现实利益。
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终止了对“规则倾向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接受。首先,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不再签署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具有比较明显“规则倾向性”的TPP、TTIP及TISA等局域性国际经济自由化协定,特朗普政府要么退出,要么叫停。其次,对于具有高度“规则倾向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特朗普不断威胁美国要退出构成该体制基础的WTO。即使美国现在并未实际退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已严重损害了WTO多边贸易体制既有的“规则倾向性”。
另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转而选择制度化程度低下的“契约倾向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目前,双边谈判已成为特朗普政府青睐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主轴。无疑,在“一对一”双边谈判中,美国可以充分发挥其实力优势,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获得更大程度打开对方市场的好处。然而,美国主导下谈成的双边经贸协定彰显的必然是具有高度“契约倾向性”的制度:第一,这些双边经贸协定不具有主体上的开放性;第二,区分不同的谈判对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将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不会追求各双边经贸协定的标准一致性;第三,随着情势的变迁,美国很可能会要求对这些双边经贸协定重开谈判,缔约双方承诺内容的稳定性将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2]。
二、美国的选择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之反动
从统治与治理的关系来看,传统的统治方式是指政府依靠权力实施强制的过程,而治理则是为弥补单一统治方式失灵而产生的一种理念,主张多元主体以形成的共识为权威基础,在确定目标的指引下,采取多样化的手段解决复杂问题。首先,统治也是治理的手段之一,治理并不全然否定统治。相应地,在国际经济治理过程中,客观上不可能完全排除实力超群之霸权国对其权力的运用。无论美国以往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还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偏好的“权力霸权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美国强权统治的因素。其次,治理必然以制度为基础。因此,美国以往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更接近治理之本义,而统治必然依靠权力。因此,时下特朗普政府偏好的“权力霸权模式”,大为扩张了国际经济治理中美国强权统治的因素。从治理的各构成要素来看,其影响所至,将导致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大倒退。
(一)治理权威基础与特朗普政府偏好“权力霸权模式”造成的危害
统治权威的最终保障来自政府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其以强制为特征,即使不被多数方认可,政府照样可以实施;治理之权威主要源于多数方的共识,其以自愿为本据,离开了多数方的认同,治理就无以真正发挥效用
[3]。
如前所示,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可强化霸权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正当性,即获得其他国家认同的程度。在以往美国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下,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呈现出了比较高程度的制度化样态。在此类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决策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仍处于不利地位,但毕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和经济收益的制度保障,这就为以往美国偏好的“制度霸权模式”下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得以持续运行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统治的权力特征既适用于国内社会,又适用于国际社会。但是,前述有关政府依靠合法垄断的权力即可实施统治的观点,实际上只存在于国内社会。因为国际社会毕竟处于“无政府状态”,哪怕霸权国再“位高权重”,也无法以自己的强权一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时下特朗普政府转向偏好“权力霸权模式”,大为扩张的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美国强权统治的因素。就此,美国赤裸裸地运用权力优势,“自上而下”地对其他国家实施单向度强制,最终必遭其他国家的抵制和反对,从而造成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在国际经济治理过程中不断流失。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时下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破坏者。这种因美国滥用权力而引发其他国家群起抗争的结果,势必打破作为国际经济治理权威来源的共识基础,从而损害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运作。
(二)治理目标与特朗普政府偏好“权力霸权模式”造成的危害
共同目标的支持,既是治理过程的归宿,又是治理实行的关键。“政府的行动靠的是正式的权威和警察的力量,治理靠的却是体现着共同目标的主动精神。”
[5]国内治理如此,国际经济治理也不例外。特朗普政府放弃“制度霸权模式”,偏好“权力霸权模式”,已严重冲击国际经济治理的目标——国际经济秩序之稳定性、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实现。
建立稳定和有效率的国际经济秩序,乃是各国的共识
[4]。如前所述,国际制度具有降低成本和带来长期、可持续收益的功能。因此,以往美国偏好“制度霸权模式”,选择更高制度化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有助于维持稳定和有效率的国际经济秩序。
对于以往美国偏好“制度霸权模式”形成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公正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历来存在争议。既有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采取市场化的“实力界定收益”之强者逻辑,对经济实力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具有内生的不公正性。但是,此类国际经济秩序又是二战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无知之幕”之后建立的,晚近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实力“南升北降”趋势的出现,依“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所获收益不断增大。随之,发展中国家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公正性获得改善的认知程度,总体上也趋于上升
[5]。
对于国际经济治理,特朗普政府转向偏好“权力霸权模式”,降低对美国的制度化约束程度,以“美国优先”战略为导向滥用强权的结果,势必严重损害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公正性。